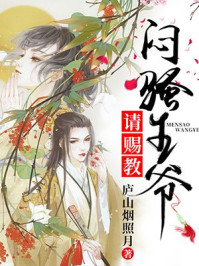她繼續說道:“在國外,人們把科學幻想分為‘硬幻想’與‘軟幻想’。‘硬幻想’是指幻想以物理、化學、生物學、天文學這些自然科學為基礎的,是‘堅硬’的科學;‘軟幻想’則是指幻想以社會學、曆史學、哲學以及心理學等‘柔軟’的科學為基礎的。這和我們的關于以‘文’為主,以‘科’為主的科學幻想小說的提法,是不同的概念。1987年上映的美國科幻大片《驚異大奇航》中,科學家把縮小到幾納米,一納米等于十億分之一米,這麼小的人和飛船注射進人體皿管,讓這些超微小的‘參觀者’直接觀看到人體各個器官的組織和運行情況。納米級的技術在當時隻是一種科學幻想,但如今已出現在現實世界。納米機器人的研發成功,就是這一嶄新技術的完美體現。有關專家預言,用不了多久,個頭隻有分子大小的神奇納米機器人将源源不斷地進入人類的日常生活。無論何時何地,通過移動電話你都能和想念的人通話。這在童話和科幻小說中的設想,如今都變為我們掌上的現實,不管你用的是諾基亞還是蘋果。激光炮利用激光作為能量,可以直接殺傷敵方人員、擊毀坦克、飛機等,打擊距離一般可達20公裡。而這一武器在《星球大戰》中也得到預想。雖然科學幻想有比較天馬行空,可能缺少一點的實際性,但是也許在不遠的未來,我們在科幻電影中看到的虛拟現實的場面将變成現實。而你說的孫悟空,能成真嗎?”
我抱歉的笑笑說:“不好意思,剛才我就是随便說說。”
她說:“科學那麼嚴謹,讓你随便開玩笑嗎!有沒有煙,給我來一根?”
這樣子,好嚣張,和她那斯文的樣子都不成正比。
我遞煙給她:“你也抽煙啊?”
她說:“我研究東西的時候,喜歡抽煙,那讓我思維清晰。”
我問:“研究什麼啊?”
我給她點上。
她抽了一口說:“剛才和你說的超能量。”
我問道:“你是說,你擁有了超能量?”
她搖了搖頭:“沒有。但有人用超能量幫助了我,讓我自身可以從光和熱中吸取能量。”
我問:“是誰幫助你的啊?”
她說道:“這是秘密。”
我和她的溝通又進行不下去了,我問到底是誰,科學家,或者什麼從書中學來的知識,還是某個超現實的人幫助了她,她都不說了。
好吧,我實在無法撬動她的口了,她什麼都不願意說。
我隻好請走了她,當然,她走的時候,我跟她們獄警說,強迫她吃喝,灌着也要她吃她喝,不然真會死掉,因為她已經徹底走火入魔。
接着,我馬上找柳智慧,原諒我的無能,除了柳智慧,還是柳智慧。
如若不是柳智慧,我也早就被開除了,像我這樣的半吊子醫生,估計隻能醫死人,我都不知道如果柳智慧走了我還能不能在這裡混下去?
柳智慧還是在排練,我去了大禮堂後,拉她過來直接就問正題。
柳智慧回答我道:“你還要弄清楚,她到底是精神分裂,還是妄想症。”
我問道:“我覺得是妄想症,難道不是嗎?”
柳智慧說道:“還不能這麼快下結論。”
我問:“有什麼分别嗎?”
柳智慧說:“精神分裂症是一組病因未明的重性精神病,臨床上往往表現為症狀各異的綜合征,涉及感知覺、思維、情感和行為等多方面的障礙以及精神活動的不協調。患者一般意識清楚,智能基本正常,但部分患者在疾病過程中會出現認知功能的損害。病程一般遷延,呈反複發作、加重或惡化,部分患者最終出現衰退和精神殘疾,少有的患者經過治療後可保持痊愈或基本痊愈狀态。妄想症,妄想性障礙,是一種精神病學診斷,是說抱有一個或多個非怪誕性的妄想,同時不存在任何其他精神病症狀。妄想症患者沒有精神分裂症病史,也沒有明顯的幻視産生。但視具體種類的不同,可能出現觸覺性和嗅覺性幻覺。盡管有這些幻覺,妄想性失調者通常官能健全,且不會由此引發奇異怪誕的行為。精神分裂,很難治療,妄想症,比較容易。能判斷出她是什麼病,才能對症下藥,如果是幻想症,把她從幻想拉回現實大多可以恢複。”
我點點頭,問道:“那她現在不說話,不配合,問什麼也不說,我怎麼和她溝通啊,她根本就不說話了。”
柳智慧說道:“你明天這個時間,帶她到這裡的換衣間,讓她自己在裡面,我觀察一下。患者獨處的時候,更容易做一些她想做的行為,我可以看看,再和她接觸。”
我高興道:“有你出馬,那一定沒事了!”
柳智慧說道:“不過,不要讓任何人知道。”
我說:“好的明白。”
下班後,我又出去了外面,外面有網絡,有wifi,有手機,有電腦,有電影,有好吃的好玩的,在這裡,太無聊啊。
出去了外面,到了青年旅社,我洗澡後躺在床上打開那台平闆電腦,物是人非啊,誰知道現在李洋洋如何如何了,是不是已經嫁為人婦了,唉,李洋洋,這也是我心中的痛,每每想到她,我都是難受。
有時候,我很想問林小玲李洋洋現在過得如何,可是我又不敢問,她過的好,又怎麼樣,過得不好,又怎麼樣。
過的好,我是替她高興。
但是想到她跟那個家夥好,我就不舒服。
過得不好,我就更不舒服。
算了,還是不問了。
不是我的,終究不是我的。
手機響了,一條信息,是許思念發來了,問我下班了嗎。
我回複:“下班了。你呢?”
她回複:“我也下班了,你吃飯了嗎?”
我回複:“沒吃。你呢?”
她回複:“我們拼飯?”
我馬上爬起來,回複:“好,在哪?”
她回複:“你想去哪?”
我回複:“你們醫院那個湘菜館就不錯。”
她回複:“那我過去點菜等你,你想吃什麼?”
我回複:“上次那些。”
她回複:“好。”
我馬上穿衣服,拿着卡去取錢。
媽的,賀蘭婷拿了我的錢,又不還我,靠靠靠。
我去取錢的時候,要經過外面那家青年旅社。
我走過去快到那裡的時候,然後突然看到一個貌似前晚爬上我窗口的一個男人。
大約三十來歲,頭發就是那個發型了,身材也像了,關鍵是那條褲子和鞋子,應該是同一個人!
他靠在一個樹後,背對着青年旅社,東張西望。
媽的,這是在等我嗎?
等我出現嗎?
真的是來跟蹤我嗎?
我決定把我當成誘餌,看是不是真的他要跟蹤我。
我從青年旅社的後邊巷子進去,然後進了青年旅社的那棟樓裡面,穿過大堂,然後出了青年旅社的門口,接着手插口袋往前走,往左轉,走向銀行。
走的時候,我留意那棵樹後面的那個家夥。
走過來了之後,我當然不能直接回頭看,我試圖從旁邊或者前面的一些反光的東西可以看到後面的情況,沒找到。
我走進了銀行,然後到了取款機面前。
取款機那裡,屏幕上方是有一個反射小鏡子的,我從那個反射小鏡子看,靠!
果然是跟蹤我的。
那家夥在門口,還是一棵樹的後面,看着我這裡。
然後,他走開了。
媽的,到底是誰找來,跟蹤我幹嘛的?
是康雪?章xx還是盧草,或者馬玲,黃苓?
靠,都有可能。
我得罪的人太多太多了。
那家夥還雙手老是抱兇的樣子,會不會我走着走着,他突然掏出一把刀就從後面捅死我,我最他媽的擔心就是這樣的。
如果真的是這樣,我死都死不瞑目。
而且死得很猥瑣,我連反抗都沒有。
我決定先甩開他再說。
等取錢了後,我急忙的出了ATM門口,然後頭不動的左右看,那家夥沒見人呢?
我往前走,看到路邊一輛計程車過來停下,一個客人下車,我忙小跑過去,上了計程車後座。
然後馬上往後看。
果然,那家夥在後面,偷偷的跟着,看我上了計程車後,他并沒有跟上來了,而是掏出手機,然後躲到了公交站廣告牌後面打電話去了。
幹嘛,叫人?
還是還有人跟蹤我。
還是向上級報告?
我感覺好危險。
故意讓司機繞着了幾條路走,然後不停看後面,看到沒有車跟來,然後在離市監獄醫院還有兩條街,我就下車了。
走路。
縮在人群中走。
就是害怕跟蹤。
總算到了那家湘菜館。
一看時間,壞了,媽的剛才和許思念說馬上到,現在都過了快一個鐘。
她估計又要生氣,她就算臉上嘴上不表現,但心裡肯定不舒服。
進了湘菜館後,我找啊找,找到了許思念所在的餐桌。
我急忙走過去,對她抱歉的笑笑:“又堵車了,不好意思啊。”
許思念說:“沒關系,隻是菜涼了,我讓老闆去熱了,我叫服務員上菜。”
我點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