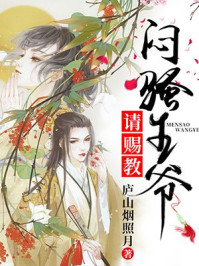既然張玫也都坦白了的說了,那我遮遮掩掩的也沒什麼意思,直接也就開門見山了。
我說道:“張玫,這倒不是說是我們的原因,你難道沒想過我們的人對付你們,是你們自己身上有原因。”
張玫說道:“知道。因為我們反反複複投降,反叛。”
我說道:“哦,你知道就好。”
張玫說道:“可我們也是為了自保,我們有辦法嗎?你下去了,别人上來,我們隻能去依附别人,你上來了,我們又隻能依附你。我們不這麼做,誰來保證我的安全,我們的利益,我們還能在這裡待下去。很多人都是無奈的。”
我說道:“呵呵,做了叛徒,反而還有理由了。你們不講感情,隻認利益,隻認錢,誰當老大,你們跟誰走。”
張玫說道:“是,我們的确不講感情,張總,誰來監獄這裡就真的隻為了那一個月幾千塊錢的死工資待着?你就是幹到死,一輩子都買不起房!”
我說道:“所以這就是犯法的理由了,被逼着去犯法了是吧。犯法說重了點,而是說你們的反叛。”
張玫說道:“對啊我們反叛了,可是你下去了之後,我們可有對付過你張總麼?”
我說道:“好像也有吧,隻是沒有幹掉我而已。”
當時我一去守門,她們的确對付我們的人,但是我們的人也不好動,她們沒轍,就沒有再動我們而已。
張玫說道:“可是現在,你上來了,不先想着對付敵人,反而是先要消滅我們,我問你張總,你覺得這樣做,很對嗎。”
我說道:“我想,假如你們上來了,你們有足夠的權利,你們要做的,也是要消滅我們吧。”
張玫說道:“不,我們最先消滅的,是女囚,是不聽話的女囚。要她們聽話。我們的目的隻是為了錢,我們對付你們有什麼用呢?況且如果要對付你們,一定鬧得兩敗俱傷,對我們來說沒有多大的好處啊。”
我呵呵一笑。
張玫說道:“我們這些人,真的就是你的敵人嗎?我們很聽話,誰上來,我們聽誰。也許你會想我們為什麼不聽汪蓉的,因為汪蓉膽子小,又不肯讓我們掙錢,她人也沒什麼本事,我們自然不會聽的。不像張總您,雄才大略,年輕有為,你一上來,我們開心得很,跟着你,有肉吃,有錢賺。”
我說道:“假如沒錢賺,你們是不是就不聽我的了。”
張玫說道:“你上來你即使不對女囚家屬送的東西和錢打主意,也能通過做生意的方式賺到錢,怎麼能說沒錢賺啊,張總您頭腦好使得很,我們都很佩服你的了。如果我們沒有能賺到錢,那一定是我們表現還不夠好,不能得到張總的喜愛。”
這張玫的嘴巴,真夠厲害的。
巧舌如簧,說話還特别能讓人心裡舒服,溫暖。
看着她那張嘴,我心想,如果是用來用的話,估計更讓人舒服。
她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心裡想法了。
她坐了更近一些,然後說道:“張總啊,我覺得我們以後還是繼續要聽你的話的,你想怎樣,我都可以讓你怎樣。”
說着對我抛媚眼,示意我可以對她肆意妄為了。
可我哪裡敢啊,萬一動手了,一群人撲進來,說我對她什麼什麼的,那就完蛋了。
這可能是個圈套。
如果沒有這個危險的可能性,我或許真的會動了她,不上白不上。
我輕輕推開了她的手,說道:“玫姐,你說的要聽我們的話,是怎麼聽的呢。”
她說道:“你要我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話的另外一句沒說,就是,你隻要不對我們下手,你讓我做什麼都要在我們能有好處的範圍之内做的事。
我呵呵一聲。
說着,她還給了我一個信封。
不用說,裡面又是幾萬塊錢。
張玫說道:“張總啊,你說撕破臉也沒什麼必要,對吧。大家同事一場,鬧起來對誰都沒好處,最要緊的,還是程澄澄她們啊。”
也是因為對程澄澄她們的仇恨,她現在更想着的是,幹掉程澄澄她們。
我說道:“玫姐,這可是大禮啊,我有種做壞事的感覺。”
張玫說道:“張總見笑了,張總有的是錢,我們這點茶錢,算不上什麼。希望張總對我們法外開恩。”
她很謙卑。
監獄長的死忠們,在求饒,在求我放過一馬。
那不如,讓她們和程澄澄她們繼續鬥下去。
我推辭一下子後,也沒敢收下這筆錢。
因為我擔心是圈套。
小心駛得萬年船。
張玫看我不收錢,那意思是覺得我在拒絕她了,她問我是不是擔心她會怎樣,我說有點吧。
她好說歹說,說她絕對不會是給我設局下套什麼的。
我說道:“哦,是吧。”
她說道:“既然你不敢這麼要,那,我讓人打進你的卡裡。”
就是監獄裡的卡上。
我說道:“呵呵。再說吧。”
她一聽,就明白該怎麼做了。
她自己打進我卡裡的錢,難道還能來說我接受賄賂不成?
反正那卡裡的錢,我先不動,就這麼放在那裡那麼一兩年再說,那我說我不知道裡面有錢,誰也不能說我接受賄賂。
除非,把我抓走打出屎來逼供,否則難查。
接着,她說道:“那以後,就多多勞煩張總了。”
利用她們來幹掉程澄澄她們,挺不錯,利用程澄澄她們來幹掉這幫騎牆派,也挺不錯。
不管誰輸誰赢,我都穩賺。
我說道:“那你想下一步怎麼做?”
張玫說道:“那要借助你的幫手了。”
我說道:“怎麼幫。”
她說了她的計劃,她打算在我的幫助下,把程澄澄集團的主要領導搞出來外面放風或者是什麼的,她們再去幹架,打架,把程澄澄她們打殘。
真的是要打殘。
不是教訓教訓而已。
一聽這個計劃,我心裡一百個不願意,這要是讓程澄澄知道我這麼幹了,她到時候肯定對付我。
我說道:“為什麼要打殘她們呢。”
張玫說道:“我們和她們打架,她們人也多,不怕死,我們打不過,但如果她們人少的話,肯定玩不過我們。前幾次姐妹們都吃了虧,咽不下這口氣,再說了不打殘,她們還能健全的對付我們。”
我說道:“那不行,這可是打殘疾了,上面查下來我很難交代。”
張玫說道:“好,那我們教訓她們一番,送她們進禁閉室,這總可以吧。”
說是這麼說,誰知道張玫到時候會怎麼幹呢,萬一她去打了人,說是教訓一番,結果是把人給打死打殘了,那黑鍋還是我來背,而且到時候她說一個是我指使或者說是我讓她們這麼做的,我死定了。
我搖頭,說道:“不,我不同意你們這麼做。”
張玫問道:“為什麼!為什麼不同意?”
她很奇怪為什麼我不同意。
我說道:“出事了很麻煩。”
張玫說道:“是擔心你自己背黑鍋嗎。”
我說道:“對。出事了,這黑鍋我背定了。”
張玫說道:“我們現在是在剿匪,消滅她們,就必須要面對面交鋒。”
實際上,我不想面對面和她們交鋒。
但如果是張玫她們自己擅自做主開打,然後出事的話,那我沒意見,雖然說我也會擔責,但是至少不是我指使的,從法律角度來說,我無罪。
打死多少人都好,都不關我的事,最多我就被監獄處分,降職。
張玫說着,就坐在了我的腿上,抱着我的脖子,然後正面擠着我,說道:“張總,你知道我們姐妹早就看她們不順眼了,就讓我們教訓教訓她們嘛。”
她撒嬌着,然後拿着我的手,放在她的腿上。
面對這樣的誘或,我經曆的太多太多,如果換做以前沒見過世面,早就淪陷,可是現在不同了,這個姿色或許是很美,但還不至于馬上就讓我淪陷。
我說道:“你先坐好。”
她說道:“不嘛。”
我說道:“這裡畢竟是監獄裡面,萬一等下有人推門進來,或是在外面聽到什麼,影響不好。”
她說道:“我們你情我願,關别人什麼事。”
我說道:“不行,這是監獄裡,要玩的話,出外面。”
她隻好坐回去了凳子,抱怨我不解風情。
我說道:“打壓程澄澄她們,我是支持的,但是不能用這麼個暴力的辦法。”
張玫說道:“哎喲張總喂,難不成,你還想說服她們讓她們好好聽你的話嗎?你看她們,都發展成什麼樣子了,簡直就是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夥,都敢和我們面對面的打群架了。再發展下去,都不知道是不是要上天,打出監獄外面去了。從來都是她們要别人聽話的份,很多獄警還聽她們話了,難道你還能讓她們聽話?”
我說道:“這些獄警,也實在是。”
我沒說下去,隻是搖頭。
張玫說道:“打我們的時候,這些獄警可是出了很大力氣了,還擅自去開監室的門,汪蓉沒有處分她們,那張總,你也沒膽處分她們嗎。”
我點了一支煙,我沒有說話。
張玫說道:“這些人可是被她們洗腦了,她們是斜教份子,難道不該處分嗎。”
我說道:“實際上,讓我來定義她們是斜教份子,是不行的,我有什麼資格,我憑什麼去定義她們,我這也不是什麼法官啊,權威部門,我能定義她們嗎。不能。”
張玫說道:“那這樣子的話,我們隻能找人去定義了。”
我問道:“找什麼人去定義。”
張玫說道:“權威部門。”
我說道:“警察嗎?”
張玫說道:“是吧。”
如果報警,讓警察來查這些人,倒是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不過,有什麼證據說明她們是斜教?
我說道:“這辦法倒是好,可是張玫啊,人家查處斜教,要有理有據,有證據。可你又有什麼證據證明她們是斜教,她們什麼都沒有。沒有宣傳單,沒有字迹,沒有筆記,沒有什麼錢财來往,她們會認罪?她們不可能會認罪。就是把她們打出屎來她們都一口咬定沒有。能怎樣?”
張玫覺得我說這話很對,于是,她說道:“那還是隻能靠我們自己。”
我說道:“你說的計劃,我不贊成。你再好好想想其他的辦法。”
她說道:“既然張總不願意,那我們隻能自己去做了。”
我沒說什麼。
我心裡巴不得你們自己去做呢。
我說道:“張玫,再好好想想其他的辦法好吧。”
張玫說道:“到時候她們也對付你們的時候,你們就後悔了。”
我說道:“喲喲喲,還生氣了呢。”
我伸手過去,安撫她,摸了摸她的脖頸,說道:“别氣嘛,我們再好好想想其他的辦法。”
張玫是可以生氣,但是生氣也不能對我發出來,因為她還擔心我對付她們,她說道:“好了我不生氣,那你可要不對付我們。”
我說道:“哪有對付你們,沒有的事。”
她這下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