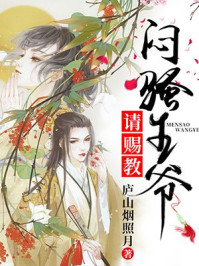離開了**,去了薛明媚管的一家酒店清吧裡面坐坐。
很久沒有和薛明媚這麼坐着聊過了。
真的是太久了。
大家都很忙,忙到沒空見面。
薛明媚要了一杯藍色電波,我要了一杯皿腥瑪麗。
雞尾酒,也還好。
度數并不是很高。
薛明媚對我說道:“如果不是因為報仇,我現在開得這些店,難道錢還不夠我花的嗎?”
她開了那麼多家美容店,還有清吧,酒吧,酒店什麼的,的确是已經夠她花的了。
人貴在知足。
薛明媚說道:“我這人不像黑明珠,沒有那麼高的追求,事業嘛,誰都想有,可是越有錢,站的位置越高,下面就越多人想把你捅下來。”
我說道:“好,我知道,你都是為了報仇,不用解釋給我聽什麼,我也不會說你什麼了。我理解你。”
薛明媚說道:“你不會理解的。為了擊垮林斌,我可以用一切的方法,哪怕是犯法,違法。可你不會,你想走正途來對付他,打倒他,告訴你,那不太可能的。我覺得你倒是忘了和他的仇恨。”
我說道:“薛明媚,我沒忘!我心裡念着這些事呢,我這不是一步一步的走嗎。”
薛明媚說道:“你身邊那麼多女人,反正嘛,跑了一個算什麼。”
我說道:“你不是我,你不會知道我心裡多難過。梁語文,是我一輩子的痛。”
薛明媚說道:“那就報仇啊,用盡一切辦法,報仇。”
我說道:“你以為我不想嗎!”
薛明媚說道:“用盡一切方法,你懂嗎。”
我點點頭,說道:“好吧,我懂。難道我就要去販毒嗎。”
薛明媚轉着杯子,說道:“太善良的人,畏手畏腳,想得太多,注定做不成事。看來我不能要求你什麼,不過我也沒指望把自己的夢想寄托在你身上。”
說來慚愧,我則是把希望寄托在了黑明珠身上。
薛明媚說道:“我現在做的這些,新開的清吧,**,這些産業其實和黑明珠沒有什麼關系。她沒有股份,我上交的,是保護費,是其他的正道的賺的錢。我另外跳出來做,但是黑明珠保護我,我還是用着她的人,就是這麼個合作的方式。你也可以這麼做。”
我說道:“我暫時還沒想要走這一步。”
薛明媚說道:“你不跳出來,不靠着自己,做什麼都是被束縛着,懂吧。隻有自己跳出來了,才能放開手腳,想做什麼做什麼,做到多大都可以!”
我說道:“是嗎?”
薛明媚建議我,反正那一家清吧我也在賺錢,幹脆就開連鎖的,開其他的,做酒店的也都成,或者跟她一起做,這并不是擺脫開了黑明珠,而是另外一種的合作方式,大家都有錢賺,何樂不為。
我說道:“我考慮吧。來,喝酒。”
一看時間,十二點多了。
我說道:“很晚了,回去了。”
薛明媚說道:“回去找女朋友?”
我說道:“倒不是,不過出來了難道不回去睡覺嗎。”
薛明媚說道:“今晚就在這裡過夜吧。”
她灼灼的目光看着我。
我笑笑,說道:“怕你。”
薛明媚說道:“怕我吃你。張隊長啊,好像每次都是你吃我吧。”
我說道:“你講話怎麼還這麼,黃!”
薛明媚吃吃一笑,說道:“不喜歡嗎。”
我說道:“男人都比較喜歡矜持一點的女人。假如是短期關系,當然最喜歡你這樣子的。但是假如想要娶回家,沒幾個人會願意娶你這樣子的吧。”
薛明媚說道:“無所謂了,也沒打算過要嫁出去。”
我說道:“想的真開。”
薛明媚說道:“我這種人,會有以後嗎。”
她好像在問我,又似乎在問自己。
我說道:“放心吧,我們,都會有以後的。”
監獄裡,貌似風平浪靜。
監獄長給我打來了電話,說有事找我,讓我去她辦公室。
我去了她辦公室,見到了她後,我問什麼事。
監獄長說在隔壁會見室,有人找我。
我警惕的問是誰。
監獄長說道:“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皺起了眉頭,假如我去了,一下子四五個男的扣着我走了,然後逼着我找柳智慧,那就完了。
我盯着監獄長,說道:“是誰。”
監獄長說道:“你自己過去看。”
她也盯着我。
能通過關系進來這裡,還能指揮得動監獄長的人,恐怕,沒那麼簡單了。
我說道:“那算了。”
監獄長說道:“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做了什麼事,總之,上面有人下來找你。”
我就更堅定了有問題,那我何必過去?
我說道:“叫他們來新監區見我!”
我轉身要離去。
監獄長說道:“你居然敢擺架子!”
我回頭說道:“不是我擺架子,而是我連對方是誰都不知道,我為什麼要見?即使我知道是誰,我也有權利不見吧。”
說完,我出了她辦公室,回去了我們新監區。
隻有回到這幾個地方,才是安全的地方。
沒想到,那人竟然找來了新監區來。
我不去見他,他自己來我監區找我了。
是一個兩鬓有點花白的大約五十來歲的男人,看這一身打扮,就知道是個當官的,貌似正義,但眼神裡卻透着精明的邪氣。
我想到曾國藩的冰鑒說的:一身精神,具乎兩目。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
盡管整體看着精神,但是看他眼神,可不是那麼正派。
來到我們監區後,我在那個比較大的會議室見了他,讓手下泡了一壺茶。
就算是敵人,也是要招待的。
我請他坐。
他一臉貌似和藹的樣子,坐下來,然後對我微微笑。
坐下後,他自我介紹了,也不說清楚,隻是說某個上面辦公室的一個負責人。
所謂的某個辦公室,應該就是xx這一類的辦公室,而負責人,沒有所謂的負責人這一說,意思就是他就是辦公室的人,就是某某大官身旁的人。
他隻給我這麼含糊介紹了之後,對我說道:“有些東西不說清楚,你也知道我的大概身份。你那麼年輕,幾年的時間,從一個管教走到今天這一步,說明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我說道:“謝謝誇獎。”
我給他倒了茶。
來者不善啊。
他連他的名字,甚至姓氏都不說,說明了根本就一點都看不起我。
想來,這副市長能耐也夠大,那麼快就找上我來了。
剛才他讓我在監獄長那邊的辦公室見他,我直接走了,估計他很不爽。
他對我說道:“你知道我找你什麼事。”
他直勾勾的看着我。
我說道:“哦,什麼事。”
他說道:“我們最近找一個人,名字,叫做,柳,智,慧。”
他還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柳智慧的名字。
我哦了一聲,然後說道:“然後呢。”
他說道:“你知道她在哪裡。”
我說道:“你們是不是覺得我知道在哪呢?說真的,不知道。”
他笑笑,說道:“如果你不把她交出來。你在監獄裡,不用做事了,甚至,命都可能沒有。給你一個星期的時間考慮。”
他說話的時候,十分的陰沉。
我點了點頭,說道:“哦。”
他說道:“年輕人,不要不懂事。你的未來長着呢,好好活着,比什麼都重要。”
說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後走了。
我看着他離去。
我點了一支煙,笑了笑,威脅我的人多了去了,他隻是其中一個。
但是目前看來,威脅我的人當中,這一個,算是最厲害的一個了。
副市長,一個代理市長職務身旁的大官,也就是這個代理市長直接對付我。
他可以用常規手段,也可以用非常規手段,總之,對付我的方法很多,很多。
怕也沒用,已經結仇了,讓我交出柳智慧,可能嗎?
即使我願意交出柳智慧,柳智慧呢,在哪。
柳智慧根本不讓我找到她,聯系到她。
突然,我感覺脊梁骨一陣涼,為什麼柳智慧不讓我找到她?
為什麼。
為什麼都是她聯系了我,才能讓我找得到她,否則我不可能主動聯系到她。
我這時候,想到了她真正的想法:柳智慧擔心我會出賣她。
對,她就是這麼想,她肯定是這麼想的,否則,她不會不讓我聯系到她。而且,如果能聯系到她,她擔心有人跟蹤了我或者追蹤我和她的通信,繼而找到她。讓我覺得脊骨發涼的是,她擔心我會出賣她,敵人會通過我找到她。
人多疑無可厚非,隻不過,她連我也不相信,她隻相信她自己。
讓我覺得脊骨發涼的并不隻有這一點,而是,如果有敵人纏上了我,她甯願犧牲我,她也要保全她自己,她要留着她的命,為了報仇,哪怕我死了,她也不能死。
想到這點,我心裡甚是難受。
為了她,我不惜與她的仇人對敵,盡管她不願意見到我這樣,我算是自找的,但是她卻是為了保住她自己,甯可先犧牲我,也許這麼說,有點嚴重,不過她心裡卻是這麼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