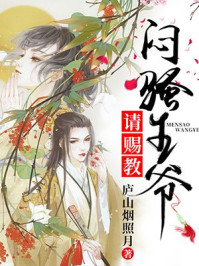無聊又看起了規章制度,看着看着,門口一陣混亂的吵鬧聲音,還有叫聲,要暴動了嗎。
我馬上扔下規章制度沖出去,要開門的時候門砰的被推進來了。
先進來的是那個長得像男人在吃飯的時候跟我說話的女獄警,後面還有兩個女獄警,押着一個女犯人。
女犯人躁狂的抽動着叫喊着:“放開我,放開!放我!”
女犯人披散着頭發,像頭暴怒的母獅子,一邊叫喊一邊要推開女獄警。
三個女獄警把她拉進來,死死按住,手铐拷在了她手上,一頭拷在凳子上,我這才發現,凳子的腳和地闆是焊死的。
女犯人還瘋狂的語無倫次叫喊:“放開我!放我出去,出去!我要出去!”
“他媽的還亂動,我等下抽死你!”長得像男人的女獄警破口大罵道。
媽的,還真的不把犯人當人看啊。
女犯人還在亂晃動聲嘶力竭的喊着,那女獄警又罵道:“好!讓你喊!用力喊!叫破嗓子最好!”
我問女獄警:“這人怎麼了?”
女獄警回答我道:“不知道發了什麼瘋。”
“是不是受了什麼刺激?”我問。
她沒好氣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才帶來給你!你把她治好,過會兒等她靜下來了我們再把她帶走。”
說完她們三就出去了。
把這頭暴怒的女獅子留給了我。
那女的嗷嗷的不知是哭是笑,然後叫了幾聲放我出去後,放聲大哭起來。
心理學導師雖然教我們如何面對各式各樣的心理疾病患者,卻沒有教我們如何面對發瘋的心理有疾病的女犯人。
我決定等她冷靜下來再和她談談。
放聲尖利的大哭許久後,她慢慢的降低了聲音,變成了抽泣。
我跟她打了招呼:“同志,你好。”
她慢慢的把頭擡起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看起來很是老實的女人,面色甚是老态滄桑,眼中含着淚,帶着絕望的無神。
“請問,是不是有人欺負了你?”我問她。
她停止了哭泣,卻不說話,把頭低了下去,歎了歎氣,用一隻手擦了臉上的眼淚。
“你有什麼不舒服的?可以跟我說說,或許我能幫得到你。”我說。
“真的嗎!?真的能幫我嗎!?我想出去!看看我孩子!”她激動了起來,身子向前傾。
看來,我是沒表達清楚我的話,我說:“我指的是心理問題。我是這裡的心理咨詢師。”
她的表情從激動變回絕望,頹然坐回座位,頭又低了下去。
“你孩子多大了?”我問。
三分鐘,五分鐘,十分鐘後,她還是不說話。
我隻好開口:“大姐,如果您不介意,可以和我說說,如果條件允許的話,我可以代你探望探望他。”
她一聽這話,徐徐擡起頭來,滿面的感激之情,徐徐說道:“謝謝,謝謝你。可是,他不在這裡。”
“真可惜。他多大了?”我問。
“五歲。”談到孩子,她的聲音慢慢帶了感情。
“很可愛吧,能不能跟我聊聊你孩子?”
大姐從狂躁發瘋,到大吼大叫,到大哭,到抽泣,到問一句答一句,到現在和我主動談了起來。
大姐姓屈,屈原的屈,她是一個農村的村姑,爹媽死的早,無親無靠的她嫁給了本村一個離異男。丈夫剛開始幾年對她還挺好,一家人種田養豬做豆腐的雖然艱苦倒也還過得去,後來兒子出生後,丈夫染了賭瘾,越陷越深,發展到後來,拿着家裡田地去賣,田地賣完後就要賣房産,房子賣了後,一夜喝醉酒輸紅了眼後回家說要拿孩子去賣,屈大姐當然不肯給,兩人在争奪孩子過程中打了起來,眼看孩子被丈夫拖出去,頭腦一熱的屈大姐拿起大剪刀就追上去一捅。
男的死了。
屈大姐雖然在村裡好人的争取下,死罪可免,但重判難逃,判了個過失緻人死亡罪。
屈大姐孩子托給了自己村裡的好鄰居照顧,而前幾天,死了的丈夫爹媽來了,以爺爺奶奶的身份把孩子帶走了。丈夫爹媽早年背井離鄉一直都在外省做傳銷,騙了村裡不少人,早就和兒子斷交,也不知道兩老到底漂在哪裡,而偏偏這時,突然回來把孩子帶走,屈大姐擔心孩子遭遇不測。說着說着,屈大姐又大哭起來:“這孩子命苦啊!”
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出跌宕起伏的戲,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我長長歎氣,可憐她的遭遇,可自己無可奈何,隻好安慰她道:“屈大姐,别太難過了,吉人自有天相啊。”
看吧,我是心理咨詢師,應該要用科學的辦法開導疏通病人才是,可我現在呢?俨然一副在大街上拿着一面旗晃着鈴铛捋着胡子穿道袍算命者的做派。
憑借我幾句話,就能解開她心結嗎,這怎麼可能。我能做的,也隻是和她聊聊而已。
門外有敲門聲,然後那三個女獄警進來了。
那個男人樣的女獄警進來看到女犯人安安靜靜坐着,笑着對我說:“哎,不錯啊哥們,你這心理醫生當得挺稱職的,這麼個女瘋子都讓你搞定了。”
我心裡頗為不爽,什麼女瘋子。就算是心裡這麼想,嘴上也不能這麼直呼出來吧。
我沒說什麼,隻對她笑笑。
她打開了屈大姐的手铐威脅道:“我警告你,你是第一次鬧,我就不關你進黑号子,要是再鬧,我可對你不客氣!走!”
屈大姐跟着她站了起來,走了兩步後,回過頭來,問我:“小兄弟,你叫什麼名字?”
“我姓張。”
她說了句謝謝你。被女獄警推搡出去。
我重重松口氣,靠在了凳子上,習慣的伸手進口袋找煙抽,但是…我身上所有的物件幾乎都被交到了警衛室,這裡哪來的煙給我抽。
站在窗口往外看,這裡就像是一座很大很幹淨的高級墳場,心裡好壓抑。
六點過了一會兒,李洋洋進來了,叫我去吃飯。
她看我臉色不好,就問我怎麼了。
我說沒事啊。
她安慰我說,剛進來的時候,她也不習慣這裡,慢慢的也就好了。
是啊,人類是很容易适應環境的高級動物,最多也就二十一天。
李洋洋又說,今晚本來要舉行的迎新活動,不辦了。
我問為什麼。
她說因為監獄出了事,有個女犯人在勞動的時候和另一個女犯人打了起來,引發了兩幫人的沖突,好幾個傷了送去了市監獄醫院,康指導員她們都去處理這事。
麻痹的,這監獄裡,還真不是個平靜的地方。
吃飯的時候,還是有不少女獄警看動物園動物一樣的看着我。
我沒像中午那樣不适應了。
和李洋洋有一搭沒一搭的聊着,李洋洋告訴我,女犯人除了關着,還要去勞動改造,而且活還挺累。
我好奇心一起,問道:“對了,你能不能帶着我去看看女囚啊?”
“不行,這是違反紀律的。”
“好吧。”說真的,我挺想去看看那些女囚幹活,睡覺的地方。
回去宿舍的時候,我才知道,李洋洋竟然就住在我的隔壁,她的舍友上個月受不了這裡的環境不做了,她就一個人住了。
我開了宿舍門,看着自己空蕩蕩的宿舍,問正在開宿舍門的李洋洋:“你平時下班回來後,做什麼打發時間?”
李洋洋一臉認真的表情說,“可以和她們打牌呀,聊天,聽歌呀,散步呀,不過十點鐘必須要關燈睡覺。
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我又想到了那個招我進來被我強行的女人,她究竟是幹啥的,是這監獄裡什麼領導?
不知怎麼的,就想到了隔壁的李洋洋。
于是過去敲了李洋洋的門,她開了門,問我怎麼了。
我說我快悶得憋死了。
李洋洋問,要不要給你MP3聽歌。
看着這個一臉純真的小蘿莉,自己真是龌龊,連這樣的小女生都**。
我看見她桌上有些書,說,我就拿些書去看看吧。
都是小女生看的書,娛樂八卦,青春校園之類的。
有勝于無吧,拿回去翻了幾頁,翻着翻着竟然睡過去了。
次日一早,爬起來洗漱後,去上班,跟康指導員報到,康指導員一副良家婦女的樣子,跟我吩咐了幾句,就叫我去了自己辦公室,就這麼定定坐着,沒人理我,也沒人來打擾我。
到了中午,李洋洋就找我去吃飯,然後回來繼續坐着,到了傍晚,李洋洋找我去吃飯,然後回宿舍,睡覺。
連續幾天,都是這樣,也沒有女犯人過來,也沒有其他女獄警,甚至連馬姐也都消失不見了,我每天能說上話的,隻有李洋洋,天呐,要是在這種環境下幹一輩子,我會瘋掉的,從來沒有感覺時間是那麼的難過。
這裡死一般的靜讓我真想跑到樓頂上大聲呼喊:我他媽的快憋死了!
他媽的,怪不得前幾個心理咨詢師都不幹了,心中突然閃過辭職不幹的可怕想法,但很快的,就壓了下去。
我家世代都是農民,農民在以前,是一個很光彩的名詞,而現在,似乎成了落後老土窮困的代名詞。家裡山清水秀,沒有一點工業氣息,沒有污染,城裡人把我們那些原始沒有開發的地方當作休閑享受的地方,我們卻早就厭倦了那裡,渴望着外面世界的精彩,渴望走在高樓大廈華燈綻放的大街上,坐着車去遊樂園公園玩。
我畢業後之所以急着找工作做,就是因為家裡太貧困,太需要我工資的支持,我們家三個孩子,我是罰款超計劃來到這個美好世界的,我有兩個姐姐,大姐大我八歲,二姐大我五歲,農村重男輕女思想,你們知道的。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沒什麼做生意的頭腦,成天鑽進一畝三分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養幾頭豬,家裡經濟就靠種地養豬支撐起來,為了生産多點糧食,父母經常天不亮就下地幹活,也就沒有多少時間來管我們,我們姐弟三的教育就放到了次要位置。
當然,這時候,兩個姐姐就是我的保護者了。
在我的記憶中,小時候家裡一直都很窮,天天吃玉米粥和青菜,到了節日才有點肉,家裡養的豬都是賣的,雞鴨除非到了中秋春節等重大節日,否則是不會輕易殺來吃的。當現在人們說玉米粥好吃的時候,我是無動于衷的,因為我早就吃傷了。
在兩個姐姐都還不到十歲的時候,她們就每天早晨天不亮起來去幫父母幹活了,她們要放牛,還要割草回來,洗漱後喝點粥吃個紅薯,然後去上學,回來後又要幹農活。可家裡的情況并沒有因為一家人辛勤的勞作而變得更好,因為兩個姐姐要讀書,我也要讀書,我還在讀高中,父母已經滿頭白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