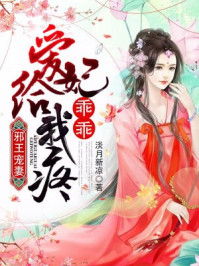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時光 第6章 懵懂的感情(1)
哥哥
你是我見過笑得最好看、聲音最溫柔的人
哥哥
天堂裡,你是否還是那顆最亮的星?
1
命運被扭轉
時間之内,你、我也許早已容顔滄桑。各自于天之涯、海之角。
時間之外,你、我依舊眉目晶瑩,并肩坐于那落滿桃花瓣的教室台階上。
我和陳勁本來是兩條絕對不會有交集的平行線,可因為他選擇了我當同桌,我們的命運有了交叉。
雖然原因不同,但是陳勁和我都上課不聽講。不過他是好學生,隻能面無表情地發呆,而我這個壞學生卻可以從發呆、睡覺、看小說中任意選擇。那個時候,我正沉迷在書籍的世界中無法自拔,所以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看小說。陳勁發呆之餘,偶爾也會用眼角的餘光掃我一眼,估計對我的孜孜不倦很困惑。後來我們熟悉一點時,他問我究竟在看什麼書,當他聽到《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薛剛反唐》《民間文學》等書的名目時,面部表情很崩潰,因為他全都沒聽說過,實在有負“神童”的名号。當聽到《紅樓夢》時,他的面色稍微正常了一點,不過緊接着又一臉不可思議地說:“‘少不看紅樓,老不讀三國’,你爸允許你看《紅樓夢》?”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愣愣地說:“我不知道,我爸爸不管我看書,反正書櫃裡有,我就看了。”
他想了一會兒,同我商量:“把你家的《紅樓夢》借給我看一下,我也借一套書給你。”
我把《紅樓夢》帶給了他,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一套四本,他拿了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詩經》給我。他很快就把《紅樓夢》看完了,撇撇嘴将書還給我,一副不過如此的表情。他又翻了一下《薛仁貴征東》,還沒看完就扔回給我。從此,都是我借他的書看,他對我的書全無興趣,我的閱讀品位在他的無意引導下從下裡巴人向陽春白雪轉換。
他借給我的《詩經》沒有白話注釋,我讀得很費勁,很多地方都讀不懂,可他從不肯解釋,隻告訴我,詩詞不需要每個字都理解,隻需記住它,某一天、某一個時刻、某個場景下,其意會自現。我不知道這話是他的父親告訴他的,還是他懶得解釋的借口。
因為讀得很辛苦無趣,所以我就不想看了,可陳勁在他無聊的神童生涯中,尋找到一個新的消遣嗜好,就是考我。他常常随意說一句,要我對下一句;或者他誦一半,我背下一半。如果我對得出來,他的表情無所謂,一副理當如此的樣子;如果我對不出來,他卻會輕蔑地朝我搖頭。小孩子都有好勝心,何況是勝過一個神童,所以在他這種遊戲的激勵下,漸漸地我把整本《詩經》都背了下來。
剛開始,我隻是他無聊時的一個消遣,但我的倔強讓他漸漸地意識到,我并不像其他的同學和老師,對神童有先天崇拜情結。于是,我們倆開始有意無意地較量着。
上過早讀課的人大概都有過這樣的經曆,一篇要求背誦的課文,老師會給二十分鐘或者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要求背下來,時間到後會抽查。在預定的時間内,誰先背會,就可以先舉手,背誦給全班聽,時間越短、精确度越高,越是一種榮耀。
陳勁從來不屑于參加此類較量,因為他的記憶力的确驚人,語文課本上的課文,他全都能背,他曾半開玩笑、半炫耀地告訴我:“把初一的語文課本拿過來,我都可以背給你聽。”所以,老師要求我們背誦課文的時候,他真的很無聊,同學們都在嗚嗚地背書,他卻捧着課本發呆。
不過,有了我這個不聽老師話的同桌,他很快就擺脫了發呆的無聊。他把不知道從什麼書上複印的文章給我看,要求和我比賽,比賽誰在最短時間内背下這篇文章。
他找來的文章可比課本有意思得多,我既是貪看他的文章,也是好勝,就答應了。從此,早讀課上,我們倆就忙着較力。比賽結果簡直毫無疑問,常常我才吭哧吭哧看了幾段,他已經告訴我,可以背給我聽了。
我怎麼都想不通,他為什麼可以那麼快地看完一篇文章。想不通,就不恥下問。
陳勁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而是用他那獨有的不屑口吻解釋了一個成語:一目十行。
在老師口中,“一目十行”一直是貶義詞,被用來罵差生敷衍讀書的态度,可陳勁說“一目十行”出自《北齊書?河南康舒王孝瑜傳》,原文是“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并不是貶義詞,是個徹頭徹尾的褒義詞,這個詞傳遞的是一種快速的閱讀方法。
我一臉茫然,不知道他究竟什麼意思。他鄙視地看了我幾眼,對我不能一點就透的愚鈍很是不屑。當時正是課間十分鐘休息時間,他給我舉例子:“你現在不僅可以聽到我說話,還可以同時聽到教室前面周小文在議論裙子、教室後面張駿的笑聲、教室外面男生的大叫聲。”
我傻傻點頭,隻要注意聽,還不隻這些聲音。
他說:“就如人的耳朵可以同時聽到四五個人的說話聲,并且都能聽明白他們講了什麼,眼睛也是這樣的,我們的眼睛是可以同時看幾行,并且同時記住幾行的内容。其實人的腦容量非常驚人,一個人腦不亞于一個宇宙。多個人同時說話,人的清醒意識覺得好像是同時,其實對大腦而言,它會自動分出先後,進行捕捉和處理。一目,是一種快速的含義,隻不過折射到時間上,快到可以忽略不計。經過有意識訓練的大腦,它的處理速度遠遠超出人的想象,所以,一目十行,對大腦而言是有先後的,隻不過對人的清醒意識而言,這個速度可以忽略到隻有一目。”
他舉手在我眼前彈了一下指,對我說:“隻這一下,在佛經上已經是六十個刹那,可對大腦而言,說不定已經被區分成上千個、上萬個時間段。我爸爸說,這世界上隻有兩個實體存在的無窮,第一是人腦,第二才是宇宙。隻要你相信它……”他指指我的腦袋,“用心地鍛煉它,它就能做到。”
我很震驚,不過令我這個傻大姐震驚的原因不是陳勁講述的内容,而是他打破了老師話語的神聖性,竟然敢完全反駁老師對一目十行的定義。
震驚完了,我暗暗記住了他的話。我在閱讀小說的時候,開始有意識地強迫自己一目掃兩行,從兩行到三行、從三行到四行……
這個過程很痛苦,但是在好勝心的誘導下,不管多痛苦,仍然強迫自己去逼迫自己的大腦運轉到極限。
不知不覺中,我的閱讀能力和記憶能力都飛速提高。我和陳勁的比賽,從一面倒,變成了我偶爾會赢。陳勁每次被我刁難住時,表情就會十分豐富,故作鎮靜、滿不在乎、暗自運氣、皺眉思索、偷着瞪我……反正任何一種都比他平時的故作老成好玩。
五年級的第一學期,我過得很愉快,首先是趙老師已經不管我了,其次我初嘗着喜歡一個人的喜悅,再次陳勁真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同桌。因為這些,我甚至開始覺得學校也不是那麼讨厭。
五年級第一學期快要結束時,有一天的自習課,陳勁突然對我說:“我明天不來上課了。”
我以為他生病了,或者有什麼事情,趙老師又正坐在講台上批改作業,所以隻是輕輕嗯了一聲。
他把我的作業本往他那邊抽了一下,示意我把腦袋湊過去。
他手裡拿着筆,在草稿紙上随意寫着,好像在給我講題:“我媽很早就想讓我跳級,我爸一直沒同意。前幾天我媽終于說服了我爸讓我跳級。上周我已經去一中做過初中的試卷,初二的數學卷我考了滿分,不過英語考得不好,隻考了八十多一點,我爸爸和校長商量後,讓我下學期跟着初一開始讀,我媽讓我退學,利用這段時間把初一其他課程的書看一下。”
“你的意思是說你再不來上課了?”
“是啊,給你打聲招呼,趙老師還不知道,我媽明天會來學校直接和校長說。”
對人人欣羨的跳級,陳勁談論的語氣似乎并不快樂。畢竟他上學本來就早,現在再連跳兩級,比正常年齡入學的同學要小四歲。小孩子的四年,心理差距是非常大的。三十四歲的人也許不覺得三十歲的人和他很不一樣,可一個十四歲的初一學生卻一定會覺得十歲的小學三年級學生和他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神童”的稱謂在某種意義上是另一種意思的“另類”,也是被排斥在衆人之外的人。長大後,我偶爾會思考,陳勁當時的傲慢是不是和我的冷漠一樣,都隻是一個保護自己的面具?
對于他的離開,我有一點留戀,卻并不強烈,畢竟陳勁和我本就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
放學後,他背着書包,在講台上站了好一會兒,沉默地看着教室裡同學們的追逐打鬧,他的眉宇間不見傲慢,有的隻是超越年齡的深沉。
走的時候,他對我說再見,我随意揮了揮手。
我趴在窗戶上,看到他背着書包,一個人慢吞吞地走過校園,邊走邊向周圍看,好似有很多不舍。周圍的男生都三五成群,勾肩搭背地走着,個子都比他高,越發顯得他矮小。
我一把拎起書包,飛快地跑下樓,追到他身邊:“我……我也回家,一起走。”
他眼睛亮了一亮,臉上卻依舊是一副什麼都不稀罕的傲慢表情。
我陪着他慢慢地走出學校,一直走到不得不分手的路口,他和我揮手:“再見了。”說完,就大步跑起來。
我沖着他的背影揮揮手,一搖一晃地繼續走着。
我們每個人都如一顆行星,起點是出生,終點是死亡,這是上天早已經給我們規定好的,可是,出生和死亡之間的運行軌迹卻取決于多種因素。我們在浩瀚的宇宙中運行,最先碰到的是父母這兩顆行星,繼而有老師、朋友、戀人、上司……
我們和其他行星相遇、碰撞,這些碰撞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我們運行的軌迹,有些影響是正面的,有些影響是負面的。比如,愛了不值得愛的人,遇到一個壞老師,碰到一個刻薄的上司,這些大概算很典型的負面相遇。而遇到一個好老師,碰到一個欣賞自己的上司,交到困境中肯拉自己一把的朋友,風水學上把這類人常常說成貴人,其實貴人,就是很典型的正面相遇。
陳勁就是我的人生路上,第一個對我産生了重大正面影響的人,這段同桌的時間,他将我帶進了一個我以前從不知道的世界,雖然還隻是站在門口,可是因為他的指點,我已經無意識地踏上了一條路。
但是當時的我,并不懂得這些,他教授我的學習方法,他課間給我講述的故事,他考我的詩詞,他推薦我聽的樂曲,他敬仰的傑出人物,所有這些東西,在當時的我眼中隻是小孩子間的遊戲,不會比跳皮筋、丢沙包更有意義,可實際上,他帶給我的東西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迹。
陳勁的突然離去,在我們班産生了很大的轟動效應,那段時間,很多女生常趴在桌子上哭泣,真是一場集體失戀。
後來,不知道是哪個執着的女生打聽出了陳勁家的地址,全班女生都很興奮,開始攢錢,計劃每個人出五元錢,湊在一起買一件紀念品送給陳勁,我沒參加,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的零花錢有限,它們有更重要的去處,比如買橘子水。
可問題是我雖不富裕,卻也絕對不窮,很多家境不好的女生都竭盡所能、傾囊捐助,我的行為在好多女生眼中顯得極其不可原諒。因為這事,我又一次成了我們班的特例,全班同學都知道我不喜歡陳勁。在我們班女生心中,這句話最準确的表達語氣應該是,你,竟然敢不喜歡陳勁?!因為陳勁,我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孤立,全班女生幾乎都視我為仇。
當時我覺得她們都好讨厭,現在想想,覺得這是多麼純潔樸素的感情,喜歡得絲毫沒有占有欲,甚至因為喜歡同一個人而更加親密,也隻有小學時代才能有這種喜歡。
陳勁走後沒多久,五年級第一學期結束了,女生們究竟買了一件什麼樣的禮物給陳勁,我不清楚,因為我在她們眼中沒有資格和她們一起喜歡陳勁,隻知道她們的确在寒假帶着禮物去了陳勁家,以至于第二學期的很長一段時間,她們談論的話題仍然是陳勁,陳勁的母親多麼漂亮,陳勁的父親多麼睿智,陳勁的家多麼高貴,陳勁是多麼優秀。
第二學期開始時,我這顆小行星碰到了另一顆對我産生重大影響的大行星。
趙老師因為身體原因,這學期不能代課,新來了一個師範中專剛畢業的高老師。也許因為是剛畢業的學生,她對工作有無限激情和創意,上課的時候會給我們講笑話和唱歌,如果有人走神,她甚至會扮可憐,對我們說:“我知道數學很枯燥沒意思,可是我在很努力地把它講得有意思,你們可以給我提意見,但是不許不聽講。”
高老師很喜歡笑,她從來不責罵任何學生,也從來不區别對待好學生、壞學生,甚至,我覺得她對壞學生更偏心,她對我們說話的時候,總是更溫柔、更耐心,好似生怕傷害到我們。
因為高老師,我不再抵觸做作業,可基礎太差,即使做,也慘不忍睹。但是,我發現每一次高老師都會把我的一道道試題仔細批改過,在旁邊詳細地寫上她對解答方法的點評,有很多我做錯了的題,她都會寫上表揚,稱贊我的思維方式很獨特,我第一次碰到錯題還被表揚的事情,吃驚之餘,不禁對高老師有了幾分莫名的感覺。
她每一節課都會提問我,如果我回答出來了,她就會熱烈地表揚我,如果我回答不出來,她總是微笑着說:“你仔細想一想,這道題目以你的能力是能回答出來的。”然後就讓我坐下。
在大人眼中,孩子們似乎不懂事,可我們的心超出想象的敏感,高老師點滴的好,我已經全部感受到。我就如同一株長在陰暗裡的向日葵,已經對陽光渴望了太長時間,正當我以為這個世界就是黑暗,我在所有大人眼中就是一個一無是處的人,不可能有任何一個大人給予我一點溫暖的關注時,高老師卻出現了,她用信任期待的目光看着我,而我卻在遲疑,遲疑着是否應該信任她的友善。遲疑中,我沒有向好的方向努力,反倒變本加厲地變壞,上她的課時,我故意看小說,故意不聽講,故意亂寫作業。她說東,我偏往西;她說西,我就向東,我想用自己滿身的刺逼出她“真實的面目”。
我至今不明白當時的自己究竟是怎麼想的,隻能約略推測出我在努力證明我的世界沒有陽光,讓自己死心,沒有希望就沒有失望,也許我隻是在用另外一種方式保護自己。
可高老師一直沒有被我逼出“真實的面目”,她用一顆父母包容孩子的心包容着我一切傷敵更傷己的行為。
這中間發生了一件事情,徹底打消了我對她的懷疑。學校為了讓高老師盡快摸清楚我們班的情況,在趙老師手術後休養期間,特意安排了趙老師和她會面,讓她了解一下每個學生的狀況。
我曆來後知後覺,聽到這個消息時,趙老師已經坐在了高老師的辦公室。當時的感覺就是一桶冰水澆到身上,一切正在心裡醞釀的小火苗都熄滅了。高老師的辦公室就在一樓,我鬼使神差地偷偷溜到辦公樓下,蹲在窗戶底下偷聽,我去的時候已經晚了,沒聽到趙老師究竟說了什麼,隻聽到高老師很客氣地對趙老師說:“……每個人都會犯錯,犯錯并不是不可原諒的事情,羅琦琦和張駿都是非常聰明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