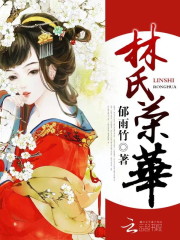盧真道:“覃颢,邵州前刺史,其先祖在唐時便為邵州刺史,後來唐亂,覃家一直世襲,但楚帝到了邵州後,覃颢幾次出言不遜,最後被革職。
”
林信:“……所以他就派人給我們開了城門?
”
鐘如英揉了揉額頭道:“你未在西南待過,不知道這邊的情況。
邵州是羁縻州。
”
她頓了頓後道:“應該說邵州以南大部分都是羁縻州,唐時對這些州縣的控制便小,基本上是由他們自選首領,刺史的權利不大,而黃氏當年自立,為拉攏勢力,将刺史之位讓給覃家,覃家就一直是邵州之首。
覃颢也不是科舉出身,同樣是世襲。
”
“楚帝與覃颢,顯然邵州百姓更聽覃颢的話,不然普通百姓也不敢因為一塊地便與權貴打架,”鐘如英笑道:“這次是我們占了便宜。
”
“可之後就不一定了,”盧真敲了敲桌子道:“楚帝革他的職,覃颢就敢開城門放我們入城,你們覺得他會聽陛下号令?
”
鐘如英道:“羁縻州的自治權向來大,除了每年向朝廷納一定的賦稅外,朝廷幾乎不管,你現在想完全控制他們是不可能的。
”
林信思索片刻後道:“甯安不亂,此時一動不如一靜。
”
“不錯,”鐘如英道:“我的意思,還是将邵州交給覃颢,不論他多麼桀骜不馴,我們都暫且忍着。
”
盧真抿了抿嘴,雖然不太贊同,但還是沒再反對,算是默認了。
鐘如英就安慰他道:“我打下的桂州同樣交給了當地的僮人,刺史就是前刺史的親弟弟,我不還是眼睛都沒眨一下?
”
盧真抽了抽嘴角道:“我總想有所不同的。
”
“那也得天下太平之後,”鐘如英笑道:“到時天下歸一,陛下下令,天下萬民皆會聽從,但現在嘛……”
現在,外來的官員隻會給當地百姓帶來變故和不安,而不論是當地百姓還是朝廷,最需要的便是安定。
林信和盧真對西南一帶都不太了解,而鐘将軍在西南經營日久,倆人便讓鐘如英去見覃颢。
覃颢很恭敬,至少面上是這樣的,鐘如英也願意賣他面子,倆人和平交談,就一些事項達成了共識。
覃颢會幫忙說服其他州縣投降,大梁為顯誠意,也會繼續用他。
覃颢在被革職不到一個月後又當上了邵州刺史,當地百姓見怪不怪,高興的慶祝起來。
沒錯,就是慶祝。
一切又回歸了,楚帝沒了,梁軍也會慢慢退去,他們的生活又如從前一樣安定下來了。
覃家是霸道,但大家都是鄉親,不像楚帝,一來邵州就要征兵,還要納軍稅,連車馬稅都要納。
可他們家裡既無馬也無車,為什麼也要納呢?
楚帝來邵州的這一個月,他們的稅賦一增再增,糧價也一漲再漲,覃大人隻是反對強征兵和多納的車馬稅便被楚帝革職,他們心裡如何能不惶恐?
現在一切回歸正軌,府衙裡還是覃颢當家,梁軍隻是過路,以後他們也不用多納賦稅,多好。
所以邵州百姓歡欣雀躍,待梁國大軍一走,便開開心心的準備過年了。
之前被抓去當兵的壯丁,還活着的都放回來的,死了的也沒辦法,他們是為楚國跟梁國打仗的,楚國都沒了,總不能讓梁國出撫恤金吧。
盧真領着大軍北上回靈州,林信押送楚國的嫔妃皇子及大臣們回京城,而鐘如英則繼續領兵南下,收複其他州縣。
其實也隻剩三個縣而已,楚帝都自刎了,縣令根本不抵抗,鐘如英的大軍才到便開了城門迎接,她去不過是換下駐軍,然後查探一下民情罷了。
各縣縣令都沒有換。
但邵州以北就沒這麼好了,各縣幾乎都頑抗,縣令大多戰死了,所有的政事都堆到了林清婉案前,她要挑選代理縣令,安排好戰後重建和救濟,還要安撫楚民,幾乎在他們攻下邵州時便是她最忙的時候。
有的縣裡好歹還遺留了個主簿或縣尉,考察過,若無大惡,就可以讓他們暫且代理縣令。
但有的縣卻是為了抵抗梁軍,從主簿到縣令都戰死,林清婉一邊要安撫縣内的百姓及他們的家人,一邊還要選出合适的縣令,别說她現在一隻手還傷着,就是全好也忙得腳不沾地。
所以一直到易寒提醒,她才想起快過年了。
她忍不住揉了揉額頭,“本來以為三兩月便能回去的,沒想到一留就是四個月。
”
“姑奶奶,陛下诏令已到,急召您回京呢,信少爺押送俘虜已回到京城,連闵尚書都回去了,您……”
林清婉翻了翻诏令,颔首道:“準備回去吧,我們就不等冉觀察使了。
”
楚國境内的戰事基本已經停了,因為梁國一路也占了不少的城池,蜀國很守信諾的按照先前簽訂好的條約,将資水以東的地方都劃給梁國。
而楚都也屬于梁國,梁帝便将這塊地方劃為荊南道,而楚都改為長沙府。
新任的荊南道觀察使姓冉,人已經在路上,林清婉便是要等他到了才遲遲不走,但人都啟程七八天了,還是不見人影,而陛下已經兩下诏令,急召她回京。
林清婉此時也不願再等了,起身道:“我們先走,正好年節将至,要緊事我都處理好了,就是暫缺幾天首官也沒事。
”
易寒點頭。
讓人準備明天上路需要的東西。
此時天寒地凍的,趕路可辛苦得很,吃食和藥材都得準備一些。
第二天一早,林清婉上了馬車,低調的出城,但還是有不少刺史府中的官吏趕來相送。
車才出了城門,林清婉便撩起簾子,對他們揮手笑道:“回去吧,難不成你們還真要送我到十裡亭?
”
她笑道:“送君千裡,也終有離别之時,不過是早晚而已。
我等共事一場,此時分離,林某便多幾句嘴,這兩月來我很欣慰,諸位皆是心系百姓,兇懷偉志之人,望将來鵬程萬裡時也不要忘了今日初衷,不要做出貪酷暴戾之事。
”
“我等不敢!
”為首的甘樸帶着衆人行禮,道:“郡主這兩月來的教誨,我等不敢忘,不敢說必廉潔如雪,卻是能奉公修身的。
”
林清婉點了點頭,笑道:“你們就此留步吧,我先走了,待冉大人來到,再替我與他說句抱歉,不等他便先走了。
”
甘樸笑,“郡主要回京城,冉大人卻是從京城而來,說不定兩位大人還能遇上呢。
”
甘樸這句笑言誰都沒放心上,可誰知他們還真就遇上了。
一行人直到傍晚才找到驿站休息,林清婉身份高,驿丞不敢怠慢,按說應該把最好的房間給她的,但他進驿站裡轉了一圈,便滿臉通紅的下來道:“林郡主,驿站裡還有幾間中房,下官讓人将房間裡的被褥等都換了新的,您,您能不能……”
易寒蹙眉,白楓更怒,雖然他們家郡主不仗勢,但也不能讓人欺負啊。
“難道我家郡主還住不起你們的上房嗎?
”
“當然不是,”驿丞彎着腰道:“以郡主的品級,這荊南道自然沒有越過您的人,可這實在是不湊巧,這上房前兩日就被荊南觀察使住了,他如今病得厲害,不能吹風,下官也不好讓他挪房間,最要緊的是,下官也怕病氣過給了您不是……”
林清婉錯愕,問道“荊南觀察使在你這兒?
”
“是,是啊,人兩日前就到了,說是路上走得急,受寒生病了,一連燒了兩天呢,現在還糊塗着呢。
”
林清婉臉色微變,就是現代發燒都有可能燒死人,何況現在?
她連忙上樓,問道:“可請了大夫嗎?
”
驿丞見她不是要問罪的模樣,連忙道:“請了,但我們這種小地方的大夫開的藥一般都見效慢,如今又是剛打完仗,藥房裡連藥都抓不齊的,偏冉大人他們帶的行李少,也沒藥,所以……”
林清婉已經推門進去了。
冉大人的侍從背對着他們正給他換毛巾,聽到推門聲,不由怒道:“不是說了嗎,我們大人現在不能挪動,憑他忒大的官兒,我們也讓不了……”
一回到看到林清婉便吓了一跳,結巴問,“你,你是誰?
”
林清婉看了他一眼,便看向床上,蹙眉道:“我是林清婉,你們家大人怎麼樣了?
”
侍從瞪大了眼睛,“林,林郡主?
這,驿丞也沒說要換房間的是郡主啊,小的,小的……”
“好了,房間的事不着急,”林清婉緩下臉色,問他道:“你家大人情況如何?
”
侍從眼淚都快落下了,冉大人的情況很不好。
他是突然收到的調令,他本是河北南道的觀察使,一個多月前收到調令,立馬便将手中的政事交給了副官,交接了小半月就趕回京城面見陛下。
等見過皇帝,拿了新的官印後就緊急出發,身邊之帶了三個侍從,可這會兒正是一年之中最冷的,冉大人也不知為什麼特别着急,路上幾乎不怎麼停歇的日夜兼程,早在四天前他就不舒服了,但還是堅持騎馬,結果兩天前人剛一上馬就暈倒了,直接從馬上摔下來。
幸虧那會兒馬還沒開始跑,不然要是行進途中這麼摔,林清婉估計是真的見不到這位冉大人了。
侍從沒辦法,将人擡進驿站裡先治病要緊,可這驿站再下去隻有一個小鎮,藥鋪連藥都不齊,更别提大夫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