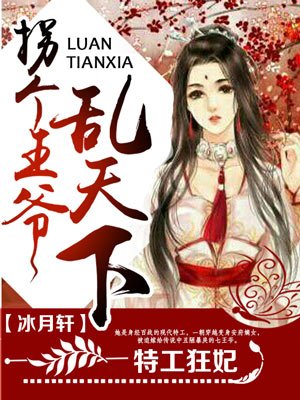“阿久,剛才那個家夥跟你說了什麼?”
慕容久久入府後,衆人就一路跟了進來,他們知道剛才百裡煜華一定說了什麼,但因為是用内力傳音,所以他們一個字也沒有聽到。
人嘛,難免八卦。
“對啊對啊慕容妹妹,不管他對你說了什麼,他不忠在先,你可千萬别原諒他,那個什麼宮雪漫,看着好看,其實心思毒着呢,你若與她喜歡同一個人,往後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呢。”
花萬枝更是如一隻花喜鵲一般,叽叽喳喳來回的說着話。
卻被蘇羽澈一臉厭棄的拉倒一邊,喝道:“小丫頭片子,你懂什麼?”
花萬枝一下不幹了,叉着蠻腰,便是一生嬌喝,“蘇羽澈,本小姐敢打包票,你現在一定還是處男吧。”
“哧……”
蘇羽澈一張嘴,險些沒讓自己的吐沫星子給噎死,這個沒羞沒臊的死丫頭,真是什麼話都敢說出來。
見他如此表現,花萬枝安心啦,“看來本小姐的眼光不錯,你果然不是沾花惹草的,不過你放心,閨房之事,我提前有過研究,待我們洞房的時候,我一定會手把手教你的。”
“阿枝呀……”
這下就連花千葉,對自家這個寶貝妹妹的彪悍程度,也微微有些吃受不住了,一臉無奈扶額道。
“這事你們私下說就好……還有,哥那有本春宮冊,前幾日從阿久師妹那借的,送給你看。”
花萬枝雙眸一亮,一聲歡叫就撲進了花千葉的懷中,“哥,你真是我的親哥呀?”
“哧……”
那邊,蘇羽澈直接皿噴三尺高,他已經徹底被這對無良兄妹,裡外夾擊成内傷,并在無修複之可能。
慕容久久也被逗了個沒脾氣,隻能有氣無力的哀嚎道:“喂,我快餓死了,我中飯都沒吃。”
真是悲慘的一天呀。
當即趕緊安排廚房做飯,要最快的。
不過當慕容久久吃飽飯後,才知道,他們馬上就要進宮了,因為今日戚族王子,秦王府郡主等人入京,成坤帝要宴請他們。
并且由他們作陪。
“戚族蠻夷,從未被冬月看進眼裡,秦王府更是自家臣子,有什麼可宴請的,而且還讓我們作陪!”
慕容久久不悅的嘟囔了一句。
聞言,花千葉笑吟吟的道:“這叫醉溫之意不在酒,或許你們的皇帝陛下,也很急迫的想知道,百裡煜華究竟在意你多一點,還是更喜歡他的那個未婚妻多一點。”
慕容久久不禁嘴角一抽。
“皇帝也八卦?”
“非也。”
花千葉搖頭,解釋道:“這些年,成坤帝一直在不留餘力的拉攏百裡煜華,可謂是用盡法子,卻一直未能真的如願。”
慕容久久挑眉,“難道這些年,百裡煜華對冬月國庫的貢獻,還不夠嗎?”
“很夠,但皇帝嘛,總喜歡牢靠的利益關系,若掌控不了,他甯願毀去,但偏偏又毀不了,那就隻好努力掌控了,阿久師妹可知這世上最牢靠的掌控是什麼?”
花千葉問。
慕容久久不屑一笑,“聯姻。”
想利用她的婚姻,攀附百裡煜華,成坤帝的确動過這個心思,隻是未能成型罷了,如今又冒出了一個宮家千金,宮雪漫。
若百裡煜華與宮雪漫順利完婚,那他就是川南宮家的姑爺,成坤帝對這個燙手又舍不得扔的山芋,隻怕是更加難以掌控。
宮家這個婚約,想阻止有些難度,但是,如果百裡煜華同時娶兩個女子過門,其中一個便有冬月的郡主,那成坤帝是否能安點心?
猜測着成坤帝的心思。
慕容久久不覺在次揚唇一笑,“那作為川南四大世家的花家,對于這場聯姻,又有什麼看法?”
花千葉幽幽搖頭,“作為花家,自然是不希望看到宮家多了百裡煜華這樣的一個助力,但是阿久師妹似乎又沒争奪之心,哎,想想也是愁人。”
他苦惱的用扇子敲了敲額頭。
慕容久久苦笑,“那我豈不是更愁,本無心嫁人,但婚姻卻已經裡裡外外的被這麼多人惦記上了。”
花千葉玩味一笑,“那你就嫁了吧,他們總不能在打一個有夫之婦的主意吧。”
說話間,他們已經到了宮門口。
今日算是小宴,所以來的人并不多,隻是幾個作陪的大臣,但當慕容久久等人下車後,卻迎面又碰到了楚王府的馬車。
若無意外,車上坐着的應該便是楚稀玉了。
果然,當一聲白衣,略有些蒼白的楚稀玉,出現在慕容久久的眼簾時,她還是忍不住沉下了臉。
嘴上責怪道:“下午剛幫你料理了傷口,你又跑出來折騰什麼?”
她口氣不善,但他卻始終眸光溫熱的看着她,道:“因為你來了,所以我也來了……今晚陛下要利用你的婚事,我怕你應對不來。”
最後一句話,楚稀玉的眸中,滿是誠懇。
卻聽花千葉諷刺一笑,“楚世子是怕阿久師妹應對不來,還是怕她突然回心轉意,晾了某些人的心?”楚稀玉擡眸看了花千葉一眼,點漆的清潤眸中,仿若含了煙霧,輕笑道:“晾不晾的倒無所謂,作為阿久的朋友,自然不希望看到她的婚姻陷入這重重的算計,就算她要嫁,也該是心甘情願的,花少主以為
如何?”
“甚好,”這是把他也防上了。
“你們在那幹嘛?進宮啊,”前面一身紅衣的花萬枝,纏着蘇羽澈,二人已經跟着引路的太監,走到了前面。
不時還能傳來蘇羽澈各種吃癟受難哀嚎的聲音。
承慶殿内。
此刻早已是燈火輝煌,酒盞飄香。
他們這一行人已經算是晚的了,乍一進殿,隻見一片華衣美服,意氣風發,因為今日被宴請的,多是年輕一輩。
戚族四王子巴布爾雖粗蠻,卻也算年輕英氣。
秦毓質依舊還是白日的那身綠衣,她并不似尋常貴女那般,循規蹈矩正襟危坐,而是單手拖着酒盞,懶懶倚在那裡。但整個人就是有種說不出的灑然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