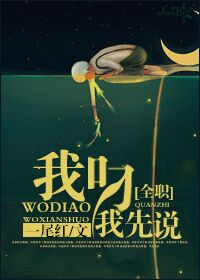錢亦繡和程月站在窗前,看到那輛馬車颠簸着向自家駛來。錢三貴被蘇四武背着和吳氏一起來到望江樓一樓,兩口子又叮囑了一番錢曉雨。
馬車直接進了前院,從車裡下來一個男人。那個男人身材修長,穿着一身靓青色箭袖長袍,腰間束着青色腰帶,還戴着鬥笠。鬥笠壓得低低的,遮了大半張臉。
錢亦錦上前深深一躬,拉着他快步進了後院。
看到那個男人,程月的身子竟是顫抖起來,眼淚也如斷線的珍珠一顆顆落了下來。她嘴裡喃喃念道,“他是江哥哥,是江哥哥,他回來看月兒了,他真的回來看月兒了……”
錢亦繡拉着她的手說,“是,是爹爹回來了。但是,他一走十一年杳無音訊,這些年裡,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咱們都不知道。娘,你可要把持住,若是他變壞了,不要咱們了,咱們就不要再理他……”
“繡兒,”程月打斷了女兒的話,淚汪汪的大眼睛滿是不可思議,嗔道,“繡兒,你怎麼能那麼想江哥哥呢?他是你的爹爹,他不會變壞的,他不會不要月兒的。”
因為生氣,還發脾氣地開了錢亦繡的手,快步向樓梯口走去。可到了樓梯口,又不敢往下走了,用帕子捂着臉哭起來,說道,“真的會是他嗎?若月兒看錯了怎麼辦?好怕啊。”
錢亦繡走過來輕聲安慰着她。
一樓,錢三貴眼圈紅紅的坐在八仙桌前,吳氏根本坐不住,站在門前往外張望着。
錢滿江歸心似箭,幾乎和錢亦錦跑着進了望江樓。吳氏一看兒子,一把拉住他哭了起來。錢亦錦把兩人拉進屋,又把門關上。
蘇四武圍着小樓轉一圈,錢曉雨坐在樓前海裳樹下的藤條椅上,也不住地往四周看着。
屋裡,錢滿江含着眼淚,把吳氏扶在椅子上坐下,就跪下給錢三貴和吳氏磕了三個頭,哽咽着說道,“兒子不孝,一走多年,讓爹娘受苦了。”
說完,又用膝蓋走了幾步,爬在錢三貴的膝上哭起來,吳氏和錢亦錦都過去抱着錢滿江哭起來。
樓梯口的程月聽到的确是錢滿江的聲音,便跑下樓去。叫道,“江哥哥,真的是你嗎?真的是你嗎?”
錢滿江站起身,轉過身看向那個依然美麗、清瘦、懵懂的小妻子,笑道,“月兒,是我,我回來了,我日夜兼程趕回來了。”
程月沖過去就撲到他懷裡,腦袋枕在他的肩上哭起來,說道,“江哥哥,你怎麼才回來?你怎麼走了這麼久才回來?爺爺他們都說你死了,還給你弄了個小墳頭。可是,月兒不相信江哥哥會死,江哥哥說過幾番花謝花開後就會回來,江哥哥是不會騙月兒的……你知道嗎,月兒天天望着門外的野花,盼着它快點謝,再快點開……江哥哥,月兒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呀……嗚嗚嗚……”
聽了她的話,錢滿江的眼淚流得更洶湧了,輕拍着她的肩膀哄道,“月兒莫難過,我沒有死,我回來了,回來看你了……”
盡管家裡人對小娘親的肉麻和直白都習慣了,但聽了這些話還是紅了臉。錢三貴咳嗽一聲道,“滿江,滿江媳婦,有些話就留着你們私下再說吧。你們坐下,讓錦娃和月兒給你們磕頭。”
程月聽了,便擡起頭對錢滿江邀功道,“江哥哥,月兒能幹,生了對龍鳳胎。繡兒乖巧,錦娃帶把兒……”
錢亦錦紅了臉,插嘴道,“娘,兒子有很多優點的,說說其它的。”
程月說,“娘知道錦娃優點多,可是,别人最看重錦娃的,還是那個優點呀。”
錢滿江笑起來,英俊的臉跟走之前的那張臉重合起來。他拉着程月坐下說,“好,讓我兒子閨女給我磕頭。”
趙成和馬護衛父子都曾囑咐他,把小主子就看成他的兒子,千成不能露了他的身份。
錢亦錦知道要給爹爹磕頭了,看妹妹還站在遠處愣愣地看着,沒有絲毫要給爹爹磕頭的意思。就過去拉她道,“妹妹高興傻了,爹爹回來了,咱們給爹爹磕頭。”
錢亦繡被他拉到錢滿江跟前,也沒跪下,問道,“你說你是我爹,那你在京城錦繡行後院附近轉過好幾次,還進了錦繡行商鋪兩次,你為什麼不跟我相認?”
見錢滿江不可思議地看着她,又說,“我養的那隻猴子是靈猴,它發現有人鬼鬼祟祟監視我家,當然要告訴我了。而且,你來一次,它就會告訴我一次。”
錢滿江想了想,便笑道,“是這樣,爹爹身上有任務,不宜在京城跟閨女相認。”
錢亦繡嗤道,“那你另外有了女人也是任務?”
錢滿江趕緊搖頭否認道,“閨女,你誤會爹爹了,爹爹沒有其他女人。”
錢亦繡還想問那個女人的事情,但怕刺激小娘親,話到嘴邊又忍了下來,以後單獨再問。
又問,“你這麼多年都不歸家,怎麼現在又突然回來了?”
錢滿江的眼圈又紅了,說道,“我在錦繡行看到你娘的那幅的繡屏,又聽了你的那些話,就再也忍耐不住了。我若是再不回來見你們,我想我會死去。經過請示上峰,又有些其它原因,就讓我回來了。”
錢亦繡冷笑了兩聲,又問,“你為什麼去給那人頂缸?是因為榮華富貴嗎?”
錢滿江沒想到女兒小小年紀問題會這麼多,還一個比一個尖銳。點點頭,猶豫着說道,“嗯,也有這個原因。”
錢亦繡的眼淚湧上眼眶,又問,“你覺得榮華富貴比家人、比父母妻子兒女更重要?”
錢滿江趕緊搖頭否認說,“不是。”
錢亦繡上前一步,看着他的眼睛說道,“既然不是,打完仗你為什麼不第一時間就回家,為什麼為了那榮華富貴去坐牢?你想沒想過,你的家裡跟别人家裡不一樣。你的父親殘疾,母親弱柔,妹妹還小,妻子懵懂,這樣一個家庭,再生下嗷嗷待哺的孩子,你讓他們怎麼活?”
說到這裡,錢亦繡的眼淚便流了出來,為這一家人吃的苦,還有那個死去的小繡兒。
她擦了一把眼淚,又繼續說,“更何況,你的妻子美貌異常,這樣一個搖搖欲墜的家庭,要護住你妻子不被傷害有多難?你想沒想過,你晚一天回家,妻子就會多一分危險,家裡就會多一分艱難?你坐了牢,又因為坐牢在京城當了官,你想沒想過,這麼長的時間裡,家裡會出現什麼變故?十一年了,你一走杳無音訊,沒給家中帶過一分一厘錢。爺爺多少次命懸一線,奶奶過早花白了頭發,小姑姑的手粗糙得像一個老婦,哥哥一歲多就獨自一人去村裡人家蹭吃食,小繡兒――我六歲前就從沒有吃過一頓飽飯,不知道肚子飽是什麼滋味……這十一年來,這個家面臨過多少危機,你想過嗎?”
随着錢亦繡的哭訴,錢三貴、錢亦錦都流出了眼淚,吳氏和程月哭出了聲。
錢滿江又傷心又慚愧,流淚道,“繡兒,是爹爹欠考慮了……有些事,的确是爹爹不能左右的。其實,這些年裡,爹爹也偶爾托人打聽過家裡的情況。聽說家中無事,便放了心。的确沒想到,你們過的如此艱難。現在,家裡所幸無事,爹爹又當了官。以後為你奶、你娘請封诰命,讓你們過好日子……”
錢亦繡斷然回絕道,“不需要你現在來錦上添花,我哥哥學習好得緊,自然會給我奶我娘請封诰命。我們現在的日子已經非常好過了,家裡的鋪子開到了京城,還稀罕你那點俸祿銀子。我娘一副繡品就賣了三千兩黃金,你一輩子也未必能掙那麼多。家裡最艱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你還回來幹什麼?”
錢亦繡最後面的一句話可謂離經判道,但她話語出格家裡人早就已經習慣了。
程月卻有些受不了了,流着眼淚說道,“繡兒,别這麼說江哥哥,他肯定不知道咱們過得不好。他在外面也不容易,定是受了許多苦……”
錢亦繡跺腳道,“娘,這個家你最應該感恩的人應該是我爺、我奶,還有小姑姑。他們跟你不是皿脈之親,卻拚上性命都在護着你。經過這麼多年的共患難,相互扶持,咱們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你不要再理這個男人,他太自私。他話說的好聽,給你留下兩個孩子就不管咱們死活。那麼多年不管不顧,因為看到繡屏就受不了相思的煎熬,就跑回來了。他一切出發點都是自己的感受,從沒有想過咱們的日子該咋過。”
又對錢滿江說,“錢将軍,你那麼大的官,肯定會找個京城的大家閨秀。你走吧,不要再來纏我娘。我娘太單純,搶不過别人的。”
程月一聽女兒不讓她理錢滿江就哭得更厲害了,說道,“繡兒,他是江哥哥,是你爹爹,娘盼了他那麼久,你怎麼能攆他走呢?”
吳氏起身幫錢亦繡擦着眼睛,勸道,“繡兒快别哭了,你爹爹在外面也不容易,他回來了就好,咱們好好過日子。”
錢三貴對錢滿江說道,“繡兒這麼難過我能理解。你看現在家裡好過,也就是這幾年,繡兒運氣好,跟着猴哥撿了些山珍賣,家裡才慢慢發起來。你媳婦姿色好,惹得好些賊人掂記,都是錦娃和繡兒想辦法,才沒讓你媳婦出事。前些年,這個家多少次瀕臨絕境,雖然最後又熬了過來,但其中的心酸我現在都不願意再去提及――苦啊。那些年,我恨不得去死,但又放心不下這一家弱小。想着,我走了,他們該怎麼辦?”
又把錢亦繡拉到他身邊倚着自己,說道,“繡兒是個好妮子,爺知道,家裡有今天,繡兒的功勞最大。”
錢亦繡就趴在錢三貴懷裡嗚嗚哭起來,錢亦錦也過去抱着錢三貴和錢亦繡一起哭。
錢滿江已經泣不成聲,起身又給錢三貴和吳氏跪下磕了一個頭說,“兒子不孝,讓家人受苦了。”又磕了一個頭說,“兒子謝謝二老,謝謝你們待月兒如親人。”
吳氏去把兒子扶起來,說道,“你是娘的兒子,不管如何,你回來了,娘都高興。”
幾人又勸惡人錢亦繡放下芥蒂,一家人圍坐在桌前訴别情。
他們聽錢滿江說了一些他的事情,他當然是有選擇性地說。錢三貴等人知道他在禦林軍裡當着從五品的官,還有見皇上、娘娘,見王爺、大臣的機會,都高興起來。當然除了錢亦繡,她還嘟着嘴,不時地橫兩眼錢滿江。
錢滿江也不以為意,閨女一瞪他,他就呵呵笑兩聲。有一次他還試圖摸摸她的包包頭,被她躲開了。而他的小妻子最乖巧了,一直任他拉着她的小手,還不時報以甜甜的一笑。
錢三貴和錢亦錦又講了些家裡事,也讓錢滿江驚出了一身冷汗。他是真的後悔了,或許當時的選擇真的錯了。孝忠的道路條,他不應該選擇那條最冒險的捷徑。閨女說得對,他家的情況跟别人家不一樣。
晚上,錢曉雨和蘇四武端了飯菜來,一家人又吃了飯,錢三貴錢滿江父子兩人還喝了點小酒。
飯後,衆人又說了一陣話,就該回去歇息了。都走到了門口,吳氏回頭問錢亦繡道,“繡兒咋不回蓮香水榭呢?”
錢亦繡裝傻地說,“我回水榭幹啥?原來每天我都陪着娘親睡的,娘沒有我陪着,她害怕。”
吳氏道,“你爹回來了,有他陪着,你娘就不怕了。”
錢亦繡固執地說,“讓我爹去水榭睡,我不去。”任憑吳氏怎麼勸,壞阿姨就是不離開望江樓。斜眼瞄到錢滿江急得一額頭的汗,想攆人又不敢說出口,心裡就一陣解氣。
程月還傻傻地用帕子給他擦汗,說道,“咱們這裡不算熱的,江哥哥咋出這麼多汗呢?”
吳氏勸了半天孫女也不聽,隻得退後一步說,“那繡兒就睡在繡房的羅漢床上,不要再去跟你娘擠。”
等屋子裡隻剩三個人,錢亦繡就對程月說,“娘先上樓去,繡兒要跟你的江哥哥單獨說說話。”
PS:謝謝親的打賞和月票,感謝!(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