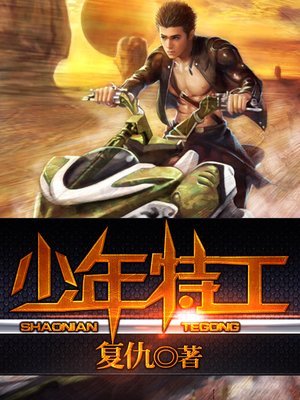一場歡宴,在楊黨的酒飽飯足進入尾聲,長街上馬車的踢踏的聲音漸行漸遠,程立微微搖着頭,笑了。
馬越渾濁的眼底還挂着一絲清明,歪歪扭扭地走了兩步,搖頭晃腦地在府門前一定,拉着程立問道:“夫子,我覺得楊黨,他有些有恃無恐。”
“呃。”說着,一擡頭,馬三郎打了個酒嗝兒。
“沒事府君,這事不就是比誰快麼,有這一頓酒宴,應當能拖延些時間,三日就夠了。”程立看着微醺的馬越,搖了搖頭對兒子程武招手喚了過來,說道:“快扶着你主公去休息吧。”
程武叉手應諾,小心翼翼地扶着馬越回房休息,這一對父子真是奇妙。通常做人家将侍從往往是爹跟了,兒子自然而然地就跟了。可程立程武不同,一開始便是程武想跟随馬越從軍,程立是根本看不上馬越,後來終于被馬越說動幫忙,卻又被馬越的尊敬推到了一個僅次于梁鹄與關羽的地位上,偏偏還不是主從。
目送着馬越被兒子送走,程立站在門口愣了一會,搖頭啞然失笑,吩咐府上侍從關好大門,轉身看着空無一人的大堂,坐在下面的蒲團上提了提未空的酒壺,猛地一大口關中烈酒灌了下去。幽州苦寒,一年的邊塞生活讓年過四旬的男人染上了酒瘾,不喝幾口身上就不舒服,奈何平日裡都要靠腦子做事,方才酒席上他是一口沒有多喝,眼下沒了事情,才敢安心喝上幾口。
夜了,也該去睡了。過了今日後面的樂子還大着呢。
馬越的感覺沒錯,楊黨的确有恃無恐,席間他說的很多馬越過去的事情連程立都不清楚,楊黨卻如數家珍。也不怪馬越擔心,程立算是看明白了,這個長安令不是那麼好對付的人,說白了,這楊黨跟自己一個樣兒,都不是什麼好人。
論起心機深沉,隻怕習慣了叢林法則的馬府君還不是那長安令的對手。
程立一邊喝着酒,一邊坐着想事情。該定的都定下來了,現在無非就看到底是誰更快一步把收集的東西送到洛陽了,眼下就看是誰的馬更快了。
回過神的時候,程立覺得一陣毛骨悚然,方才他帶着些許的酒意竟未發現廳堂上還有别人,悠然自得地小口飲着酒突然對上一雙憂郁的眼睛讓他渾身寒毛一炸,他見過這個孩子,跟馬越有着幾分相像。
堂中角落裡,滿眼憂郁的少年微微皺着眉頭盤腿背靠着柱子,燭火的燈光打不到這裡,隻有身上重重疊疊的陰影,就那麼抱着一柄生了鏽的鐵槍,眼睛冷冷地看着自己。
程立沒有放下酒壺,他看到這個長得跟馬越有幾分相像的孩子便已經猜到是馬越的族人,但他還從未聽過馬越有個胞弟,在印象裡涼州馬氏三兄弟府君是最小的那個,那這個是……
“孩子,你是府君的弟弟?”
馬超搖了搖頭,沒有說話。
這是他到長安的第七天了,七天裡馬越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也顧不上他,聊了聊天他卻不願說太多,有些事情埋在自己心裡就好,沒必要說出來。可他覺得自己應該做些什麼,為小叔做些什麼。
在他面前喝酒的這個老頭兒,在馬超心裡就是個好對象,他不知道三叔在老頭兒來之前是什麼樣子,但在這個老頭一過來,三叔便開始了不少大動作,一下子把府裡幾乎所有人都派了出去,連武藝不錯姓鮑的漢子也派了出去,整天跟這個老頭兒關在屋子談事情從白天到黑夜……他看得出來,三叔很倚重這個威武的老頭兒。
程立看着默不作聲的馬超愣了一下,他突然想起來,府上說府君的侄子來的當日便将門下最剽悍的京兆遊俠鮑出擊敗,莫非這是府君的侄子?
“你是馬超?”
馬超聽到這個被三叔倚重的老頭兒說出自己名字,眉毛輕輕挑了挑,心裡有些喜色卻沒有笑出來,隻是十分冷靜的搖了搖頭。
“老夫聽說,你擊敗了鮑出?鮑出的武藝怎麼樣?”程立一面問着,其實他還有個計劃,隻是缺少一個勇武之士實行,本來他打算今晚讓程武自己出去的,但看到這個跟馬越長得十分相似的少年時改變了主意,程武說過,硬拼的話他的武藝跟鮑出差了一線,如果府君的侄兒能打敗鮑出,多一個高手便多一分成功的幾率。“孩子,走的近些,讓老夫看看你的模樣。”
馬超提起鐵矛向前走了兩步,盤坐在程立三步之外。
程立看出,面前的這個孩子遠遠不像馬越那麼自信正直,眼睛裡埋着一層深深的憂郁,面容上與臉上沒了疤的馬越十分相似,可看上去确實截然不同的感覺,這孩子,戾氣太重了。
就在程立發愣的檔口上,馬超開口了,聲音帶着些許沙啞,“老先生,您是叔父的幕僚。”說着,馬超愣了一下,他不知道這個詞該不該這麼說,他曾聽父親提到過韓遂以前差點做大将軍府的幕僚,“是幕僚嗎?”
準确來說,馬超甚至還不是很明白幕僚是個什麼意思,他不知道,幕僚幕僚,幕府中的官僚。
他的叔父,可不是什麼大将軍。
不過顯然面前的老頭兒并不在乎這些虛名,若在乎虛名也就不必跟着馬越颠沛流離地為了一個承諾遠走幽州了。程立隻是摸着胡子笑着點頭,勉強算是認同了這個說法。
馬超躬身便拜,擡起頭來對程立說道:“還請先生教我,怎麼能為叔父分憂!”
馬超的想法跟馬越幾乎是不謀而合,可就在即将說出的這一刻程立卻遲疑了,他在想一件事……七天前馬越給所有人分派任務,唯獨沒有給馬超和自己父子,這之中肯定有他們背井離鄉不了解京兆尹情況的原因,但程立也不禁會去想,馬越是不是不想讓他這個大侄子去做事情呢?
馬超依然皺眉頭看着程立,一雙劍眉斜刺出去,大概是十幾歲開始一直皺眉,他的眉心總有幾道皺紋,看上去總是分外嚴肅。
“那個先前在府上喝酒的楊黨。”程立斜指着門外,仿佛楊黨就在外面似的,小聲對馬超說道:“你跟老夫那犬子牽上馬看着他府上向洛陽傳信的人,他們手裡有對你叔父不利的消息。”
“諾。”
馬超點頭,提起鐵矛便向外走,程立急忙喊住他說道:“你先等等,兩人一起。”
馬超沒有說話,點了點頭,徑自走出堂中繞到馬廄尋一匹看得上眼的馬匹。
在馬超眼裡,三叔這兒的馬,清一色的都是劣馬……除了那匹鮮卑青駒,那是馬越的坐騎。馬超看着青駒眼神中流露出渴望,卻不敢騎,隻是隔着栅欄看着這匹馬。
“你想騎這匹馬?”
馬超轉過頭,是一身甲胄滿面笑容的青年,馬超沒說話。
“我是程武,阿父讓你我二人一同,那便一起。”程武自顧自地牽起旁邊的一匹幽州黑馬也不管馬超不愛說話,很普通的腳力戰馬,套上鞍鞯轉頭對馬超笑道:“想騎的話就騎吧,借府君的馬騎一下也沒什麼大不了。”
說着,程武挑了挑眉毛,笑了。在他印象裡馬府君那麼和藹,别說是叔侄兒,就是府中随便一個下人想借馬騎都不會介意,很難想想馬越對什麼身外之物吝啬。
馬超的手幾乎要觸及馬鞍,他卻還是停下了,轉過頭,義無反顧地抓起一匹平淡無奇地灰毛戰馬的鬃毛,不套籠頭,不着鞍鞯,就像是對剛在草原上套來的野馬一般,柔順地牽着馬倒提着鐵矛便出了馬廄。他總是這樣,人說怎麼樣是可以的,如何做沒有關系,他便偏偏要照着另外一個方向去做,沒有誰能命令他,沒有誰能告訴他這件事他該怎麼做。
他有自己的想法,即便……是不好的,也勸不住。
程武牽着黑馬跟在馬超後面出了馬廄,問道:“你怎麼不放鞍?”
“涼州人騎馬不用鞍。”馬超的聲音有些冷,他不是很喜歡這個叫程武的青年,話太多了,像馬岱一樣。“長安去洛陽隻有一條大道,你守在他們門口,看到人出去跟着就好,我去官道上等人殺。”
說着,馬超跨上戰馬,脫下罩袍一卷鐵矛夾在腋下,身子一趴抓着鬃毛便在長安城中奔馬而去。
這一手騎術,來得高!看着夏夜裡穿着皮襖的倔強背影,程武啞然失笑,府君的這個侄兒,可是有一手的好本事。可有時候,好本事也意味着難伺候。
甩了甩頭,程武不再瞎想,從馬背上取出麻布罩袍披在身上擋住一身甲胄,牽着馬小步向着楊府溜兒着過去。
夜晚的星空很明亮,夜裡帶着一點寒氣,像是去年在幽州的日子。一年有餘的幽州之行,讓他的心更加堅韌,無論是軍略還是政事都有了很多實踐的機會,盡管更多的時候他處理事情仍舊是破綻百出,但多少要比從前躲在東阿縣傻讀書要強上一些,畢竟有從前程立悉心教授的種子在,無論什麼事情上手總要來得容易的多。
隻是不知,這一夜是否平靜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