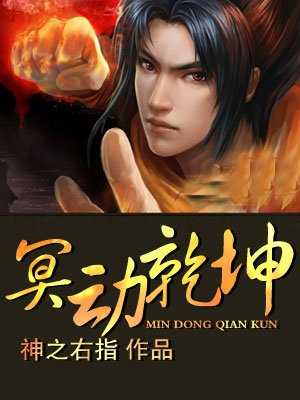侯懷安拿出一筆不菲的銀子,求柳氏的爹爹為他們帶路。
柳氏的爹娘貪财卻又不願出力,便指使女兒代勞。
柳氏那時是個青春少女,為人爽朗熱情,毫不猶豫就答應了侯懷安的要求。
柳氏帶着他們走出沙坑,離家已是百裡開外。
在一天晚上,風流倜傥的潇灑公子侯懷安,借着酒勁鑽進柳氏的小帳篷**了她。
柳氏尋死覓活,立要拼命,侯懷安逢場作戲便答應了要娶她。
在一個小鎮客棧裡,兩人同宿七天七夜,她為他忙裡偷閑趕制承載兩人情義的荷包。
第七天晚上,柳氏做活累了,一覺醒來,駝隊渺無蹤影,炕頭上放着一袋金銀首飾。
侯懷安歎了口氣道:“我的身份定國公也知道,是不可能娶為妻的?
隻有一走了之,這一走就是二十年!
”
後面的事情,張寶兒大概也可以猜測個八九不離十:柳氏醒來的時候,本以為侯懷安還會回來,便寄身旅店,苦苦等待。
兩個月後,她發現已有身孕,想回家顔面無光,又情系遠方,呆在這兒吧,難免光棍欺壓,衆口糟踐。
萬般無奈,她隻有到另外一個地方,隐姓埋名,盼望奇迹出現。
女兒降生後,柳氏又苦等了五年,才不得不承認自己是被人騙了。
她徹底絕望,侯懷安腿間那塊醜陋的紅痧胎記如一塊燒紅的烙鐵擱在她的兇口上,無日無夜灼燙着她,讓她痛不欲生,她惟一的選擇便是使那塊紅色從人間徹底消失。
她認為任何殘忍行為都無以消弭她對那個男人的刻骨仇恨,她終于想出了這樣一個辦法。
她不僅要消滅他的肉體,還要粉碎他的靈魂。
于是,柳氏讓女兒去跟獨狼學武,告訴她腿根部有紅痧胎記的那個男人就是奪走她父親的的仇人,讓她去找到這個男人并親手殺死他。
對一個女人來說,這是多麼大的仇恨,甚至不惜讓自己的女兒去親手殺了親生父親。
張寶兒有些同情侯懷安了,他問道:“既然侯兄知道黑蠍子是你的女兒了,打算怎麼辦?
”
“我能怎麼辦?
”侯懷安苦笑道:“當年我不能娶她的母親,是因為我有我的苦衷,現在我依然不能與她相認!
”
張寶兒想勸勸侯懷安,可卻不知該怎麼開口。
侯懷安一臉痛苦道:“就算我認了她,可她今後如何與我相處呢?
與其讓她痛苦一輩,還不如不相認的好!
”
侯懷安說的不是沒有道理,這些年來,黑蠍子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尋找仇人報仇。
如果有一天,她突然知道自己的仇人就是親生父親,她是報仇還是不報仇呢?
恐怕這一輩子她都會在痛苦和矛盾中度過了。
侯懷安盯着張寶兒道:“定國公,侯某求你一件事!
”
“侯兄不用說了,我知道,我會替侯兄保密的!
”張寶兒接口道。
“定國公,我說的不是這件事情!
”侯懷安鄭重道:“我想求定國公,昭武九國的事了之後,求定國公将她帶回長安去,今後給她找個好的歸宿,我将感激不盡!
”
“讓我帶走?
”張寶兒吃驚的看着侯懷安:“你把女兒交給我,會放心?
”
侯懷安點點頭道:“或許有一天我們會在戰場上相見,甚至可能會死在對方手裡,但有一點侯某堅信不疑,那就是定國公的為人。
把她交給定國公,我一百個放心,至少也可以讓我的愧疚減輕一些!
”
張寶兒苦笑道:“侯兄,你這也太高擡我了,我可沒你說的那麼好!
這事嘛……”
侯懷安驚喜道:“定國公答應了?
”
張寶兒歎了口氣道:“我能不答應嗎?
”
……
回到大佛寺,張寶兒徑自來找宏德主持。
張寶兒将大食人的圈套講于了宏德主持,最後自責道:“是我之前考慮不周,主持可萬萬莫去與大食人講法,以免中了他們的奸計。
”
誰知宏德主持人聽了卻波瀾不驚道:“施主所說的貧僧心知肚明,貧僧乃佛門中人,貧僧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佛陀曾于《悲華經》中說,‘慈心即是助菩提法,于諸衆生心無礙故。
悲心即是助菩提法,拔出衆生諸苦故。
喜心即是助菩提法,愛樂法故。
舍心即是助菩提法,斷憎愛故。
’慈悲喜舍,一旦從心底湧現,便能點亮生命之光,照徹幽暗娑婆。
施主就不必勸我了,修行不是口說,而是要用心去做。
我佛釋迦牟尼佛修行時可以割肉飼鷹、舍身投虎,貧僧這副臭皮囊,老病死之後,轉瞬間即腐敗臭爛,有何舍不得的?
既然大食人要,就布施給他們吧!
”
張寶兒聽罷,頓時愣住了:侯懷安猜得真準,看來自己是無法勸得動宏德主持了。
此時正是康居城最冷的季節,半空時不時有狂風絞動,呼嘯着帶起千百道砂龍,卷舞在綠洲上方,吹得胡楊樹簌簌作響。
這一天上午,萬巷人空,康居城内的百姓都彙聚到了王宮前的廣場上,觀看隆重的佛教與大食教的論法。
百姓們暗暗祈禱祝福:希望宏德主持能大展風采,讓大食人知難而退,畢竟這關系到每一個人的未來。
王宮門前的台階上,站立了一長排的人。
居中的并不是總督屈底波,而是蘇伽,屈底波與康國國王突昏分列在他的左右兩喧。
除此之外還有康國宰相提契、突昏的弟弟居以及有康國的官員與大食軍的将領們。
宏德主持今日特意穿了一件新的袈裟,在大佛寺衆弟子的簇擁下,他來到法壇之下,在弟子們的目送中,宏德主持淡然走了上去。
到了法壇之上,宏德主持盤腿坐下,雙手合十,眼觀鼻,鼻觀口,口觀心,輕聲誦起《大乘經》來。
大佛寺衆弟子也同樣盤腿坐下,跟着宏德主持誦起經來。
法壇上下頓時嘹繞着節律抑揚的誦經聲,響徹耳畔。
大佛寺衆僧與其說是誦經,不如稱之為唱經。
他們唱經的聲音,來自喉嚨的深處,甚至是肺腑,清晰而低沉,綿綿不絕。
尤其是領經的宏德主持,其聲音更讓人驚歎不已,那絕對是一種獨具穿透力的吟誦,無須經過耳膜便已觸及心靈。